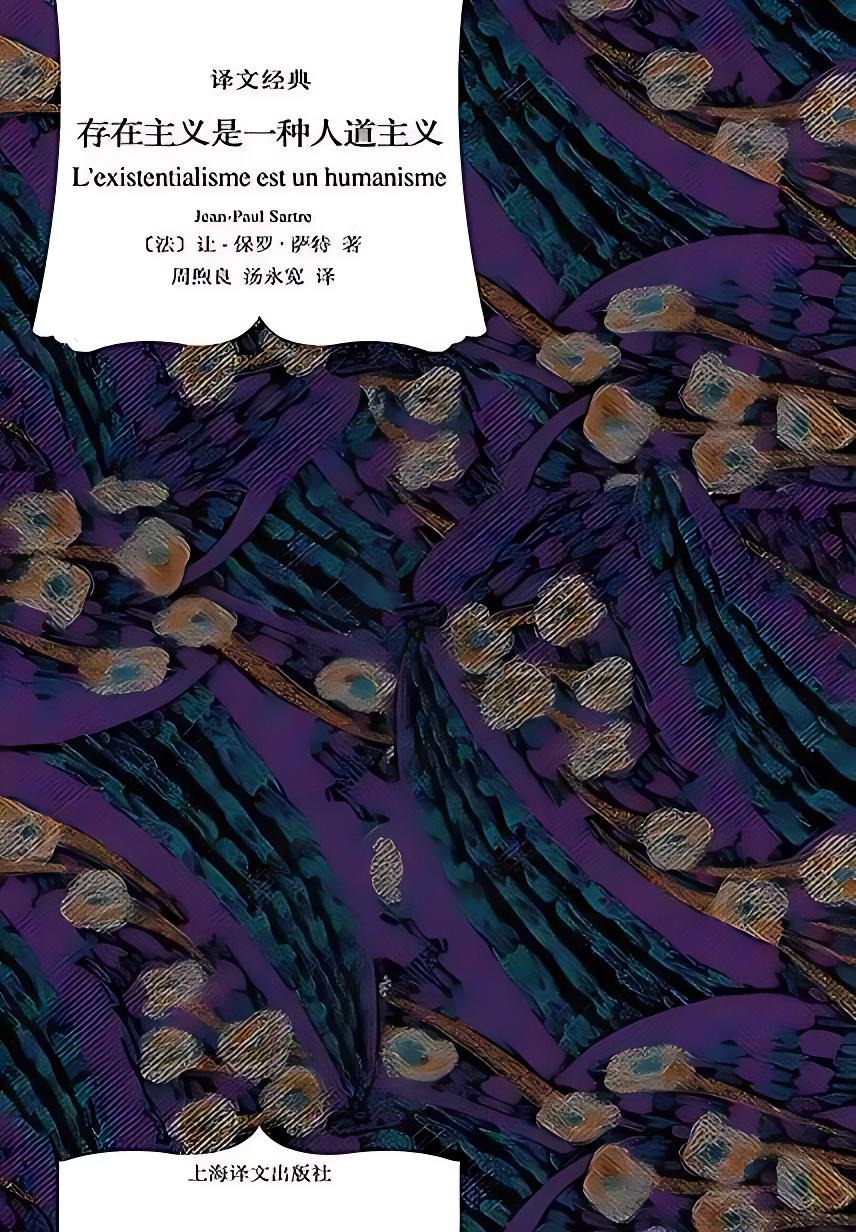
读后感
“存在先于本质” 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提出的重要哲学观点。
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
想象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来到世上,这就是 “存在”,你首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成长过程中,你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图案、书写故事,这些选择和行动就构成了你的 “本质”。
比如,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面临职业选择。
他可以选择去当老师,通过不断备课、授课,关爱学生,逐渐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知识渊博的教育工作者,这就是他通过选择和行动塑造出的 “本质”。
他也可以选择创业,在商海中拼搏,经历成功与失败,塑造出勇于冒险、有商业头脑的 “本质”。
他不是生来就被定义为老师或者企业家,而是先存在于这个世界,然后通过自身选择和行动,才赋予自己相应的本质。
这一观点强调人的自由和责任。
因为我们的本质由自己创造,所以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同时,我们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是我们的选择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就像画家要为自己在画布上创作的作品负责一样,我们要为自己人生这张 “画布” 上呈现的一切负责。
听起来很唯心主义,很像《了凡四训》里提到的,人生来并非是定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
这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你不可以光有选择,而不去承担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都由你负责。
毕竟,人们习惯于在错误的结果面前,从别处寻找借口,而不是直面自我的抉择。
并且,要明白不要怀抱希望行动。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这一点就很像斯多葛派的观点,一些事情我们能控制,另一些则不能。
在书中,萨特还提到,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
人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厄运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在于你怎么看待。
这一点也很像斯多葛派的观点,伤害我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萨特还认为,不是情感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定义了这种情感。
书中有一个例子,男子是要陪母亲在家,还是选择去参军。
如果说因为爱自己母亲选择在家,那他用什么证明呢?只能真的是陪自己母亲在家这个行动来证明。
那他同时也就没办法证明,他真的是想要参军的,即便他内心深处确实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想要陪自己母亲的这个情感,和他为了逃避参军,选择陪自己母亲这个私心,在外人看来,行动是一致的,都是陪自己母亲,但是,这两者的意图并不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例子,我自己的理解是,还是强调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一要点,而不是推卸责任和找借口。
比如,我是因为爱自己母亲,所以选择陪她,才不选择参军的,你要理解我的苦衷。
但是,对于别人而言,是没有义务去理解你的苦衷的,从一开始,你就已经选择了,所以是什么结果,都应该要面对和接受的,而不是要求和指责他人。
这让我想到了薛定谔的猫,在你没去选择之前,你可以是陪母亲在家,也可以是去参军。
但是,在你做出选择之后,你只能是陪母亲在家或者去参军,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正如,人们无法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能既要又要,那我们就要谨慎对待做出的选择,以及想明白选择的后果,是否可以承受。
但只要你做出选择,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摘抄
- 让-保罗·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
- 是什么使他这样深深受到法国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文学?他的哲学?还是他的一系列正义的言论和行动?回答是这一切都包括在内。
- 在他说来,先是有人,然后通过人的自由选择的行动,人才成为他那样的好人或者恶人。英雄或者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的主动选择使他成为英雄或者懦夫。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论点。
- 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
- 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
-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则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没法避免选择,他不选择也等于作出选择。所以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即使不能有力地树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至少可以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而这种哲学在经受过法西斯铁蹄蹂躏、精神状态处于瓦解状态的欧洲,是有其一定的吸引力的。
- 晚近。
- 存在先于本质——或者不妨说,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
- 裁纸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制造出来的物件,又是一个达到某一固定目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质,也就是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
-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都说不上的。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
-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 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 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作的自觉决定。
- 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 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 主观主义一方面指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
-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
- 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模铸自己形象的同时我们要存在下去,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对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我们的责任因此要比先前设想的重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 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
- 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
-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
-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会随即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 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
- 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
- 人的确是被逼处此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仍旧自由自在,并且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 人是人的未来。
- 康德的伦理学说,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
- 如果我和我母亲呆在一起,我就是把她当作一个目的,而不是当作一个手段:但是根据同样理由,那些为我战斗的人就有被我当作手段的危险;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去帮助那些战士,我将是把他们当作目的,而犯了把我母亲当作手段的危险。
- 如果价值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价值太抽象了,没法用它来决定我们目前所考虑的特殊的、具体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
- 当我看见他时,他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如果我觉得非常爱我的母亲,愿意为她牺牲一切——诸如报仇的意志,以及一切立功立业的渴望——那么我就同她呆在一起。如果相反地,我觉得对她的感情不够深,我就走。”但是人怎样估计感情的深浅呢?他对母亲的感情恰恰就是以他站在母亲这一边来衡量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某个朋友爱到可以为他牺牲,或者牺牲一笔钱的程度,但是除非我这样做了,否则我是无法证明我爱他到这样程度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母亲爱到同她呆在一起的程度”,但只有我真正同她呆在一起时才能这样说。我要估量这种感情的深浅,只有付诸行动,以行动来说明和肯定我的感情的深浅。但是如果我再援引这种感情来为我的行动辩护,那我就是卷进一种恶性循环。
- 正如纪德说得好,一种伪装的情感,一种真挚的情感,两者是很难区别的。决定爱自己母亲而同她呆在一起,和演一出喜剧其结果是同母亲呆在一起,这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
- 情感是由人的行为形成的;所以我不能参照我的情感来指导行动。而这就是说我既不能从内心里找到一个真正的行动冲力,也不能指望从什么伦理学里找到什么能帮助我行动的公式。
- 在你选择一个人向他请教时,你作这项选择就已经承担责任了。如果你是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请教一位牧师;但是牧师里面有法奸,有参加抵抗者,有等待时机者;你选择哪一个呢?这个青年如果选择一个参加抵抗的牧师,或者选择一个法奸牧师,他事先就得决定他将会得到什么忠告。同样,在来找我之前,他也知道我将会给他什么忠告,而且我只有一个回答。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
- 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
- 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还得我自己去理解这些标志。
- 人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厄运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他还是去当木匠,或者参加革命的好。不过,就解释标志这一点来说,他是承担全部责任的。这就是“听任”的涵义,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而随同这种听任俱来的就是痛苦。
- 至于“绝望”,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极其简单的。它只是指,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一个人不论指望什么,这种可能性的因素总是存在的。
- 没有一个上帝或者什么先天的规划能使世界和它所有的可能性去适应我的意志。
- 当笛卡儿说“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世界”,他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即我们不应当怀着希望行动。
- 我不能够依赖我不认识的人,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
- 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
- 说实在话,事情是由人们决定要怎样就怎样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将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呢?不。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的承担责任行事,根据那个古已有之的公式:“从事一项工作但不必存什么希望。”这也不等于说我不应参加政党,而只是说我不应当存在幻想,只应当尽力而为。
- 如果我问自己:“这样的社会理想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呢?”我没法说,我只知道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 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
- 许多人郁郁不得志时只有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办法,那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这人碰见的事情总是不顺手,否则我的成就要比过去大得多。诚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我真正爱的女人,或者结识过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不过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值得我结识的男人,或者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女人;如果我没有写过什么好书,那是因为我过去抽不出时间来写;还有,如果过去我没有什么心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找到可以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所以我的能力、兴趣和能够发挥的潜力,是多方面的,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因此决不可以仅仅根据我过去做的事情对我进行估价;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等闲的人。”
-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
- 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 如果有人攻击我们写的小说,说里面描绘的人物都是卑鄙的、懦弱的,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的作恶者,那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卑鄙的、懦弱的、恶的。
- 假如像左拉一样,我们把这些人物的行为写成是由于遗传,或者是环境的影响,或者是精神因素、生理因素决定的,人们就会放心了;他们会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谁也无能为力。”
- 存在主义者在为一个懦夫画像时,他写得这人是对自己的懦弱行为负责的。他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懦弱的心,或者懦弱的肺,或者懦弱的大脑,而变得懦弱的;他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生理机体而变成这样的;他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懦夫的。
- 世界上没有懦弱的气质这样东西。
- 使人成为懦夫的是放弃或者让步的行为;而气质并不是一种行动。一个人成为懦夫是根据他做的事情决定的。
- 人们喜欢的是,一个人天生就是懦夫或者英雄。
- 如果你天生是个懦夫,你就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因为你对此毫无办法可想,而且不管你怎样努力,你将终身是个懦夫;而如果你天生是个英雄,你也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你将终身是个英雄,像一个英雄那样吃吃喝喝。而存在主义者却说,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事例或者某一特殊行动就作为你的全部。
- 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而惟一容许人有生活的就是靠行动。
- 我思故我在。
- 为了说明可能性,人必须掌握真理。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到自己。
- 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了别人。
- 人的历史处境是各不相同的:人生下来可以是异教社会里的一个奴隶,也可以是一个封建贵族,也可以是一个无产阶级。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生存在世界上所少不了的,如不得不劳动和死。
- 这些限制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或者说,既有其主观的一面,又有其客观的一面。客观是因为我们到处都碰得见这些限制,而且到处都被人看出来;主观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而如果没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联系这些限制而自由地决定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这些限制就是毫不足道的。
-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
- 先讲第一种:说不管我们怎样选择都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某种意义上,选择是可能的,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我总是能够选择的,但是我必须懂得如果我不选择,那也仍旧是一种选择。
- 我们的看法是,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他或者仍旧独身,或者结婚而不生孩子,或者结婚并且生孩子。反正,不管他怎样选择,鉴于他现在的处境,他是不可能不担当全部责任的。当然,他选择时用不着参照任何既定的价值,但是责备他随心所欲是不公平的。我们不妨说,道德的抉择比较像一件艺术品的制作。
- 这话先说清楚;然后我们问,当一个画家作一张画时,可有人责备他不按照先前建立的法则作画的?可有人问过他应当画什么画呢?谁都知道,没有什么预先说清楚的画要他画的:画家自己从事作画,而他应当作出的画恰恰就是他将会画出来的那张画。谁都知道先天的艺术价值是没有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一张画在布局上,在创造的意图与成品之间,是有好坏可言的。谁也说不了明天的绘画将是怎么样的;谁也不能在一张画完成之前对它说长道短。
- 不论是懦夫或者小人,离开了存在先于本质的严格可靠性这个水准,都是无法识别的。
- 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
- 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连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正确证据也救不了他。
- 每个人都认为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无论什么,只要与他,或者与他所属的社会团体利害有关的事,都是在取得实现的过程中,而且对他和构成他那个社团的人们也必将是有利的。
- 绝望不是希望的对立面。
- 每个人,在他每时每刻都怀有的理论的或实际的——例如涉及政治或教育的问题等——目的之外,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一个我想称之为超越一切的或者绝对的目的,而所有这些实际的目的只有在与那个目的相关联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一个人的行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因人而异,但又都具有这种特质:它是绝对的。因此,不仅是失败,希望,在下面这个意义上也是为这个绝对目的所制约的:那就是真正的失败关系到这个目的能否实现。
- 我相信我或多或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它有多大价值就是多大价值。
- 不管怎样,在历史的许多运动中总有一种运动会慢慢地引导人认识自己。于是,本来会在过去实现的一切就会发生,就会具有一种意义。比如,我所写的作品。那就是给予我们所做出的一切以一种不朽。换句话说,人们必须相信进步。而这或许是我最后的一句天真的话。
- 人们应该认识到一个政党并没有真理,并且也不指望有真理;政党自有其目的意图,并向某个方向进展:一个同路人,确切的意思就是“一个试图在这个党的组织之外思考问题而希望党能利用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人”。
- 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一个真正选定的机构,在那里每个人(person)都将成为人(man),其中一切集合体都同样地富有人性。
- 你不妨注意这一点:尽管你以掩藏自己的存在而谈论我这种方式参与这次对话,我们仍然是在一起进行的。
- 在只有一个作者的时候,思想就带有它自己的印记:一个人进入作者的思想,这个人就循着那位作者已经探出的那些道路行进,尽管这个思想是普遍的。
- 我们共同形成的这些复性的思想总是给予我一些新的东西——尽管从一开始我表示赞同过。我曾想不管你能说什么来改变我的一个观念,不管你说的是你的反对意见或者是一种对观念的不同看法,等等,那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不再把我放在一种从一张纸的后面想象出来的公众面前了——我以前经常这样——而是放在那种能引出我的观念来的反作用的面前。
- 政党制度是左派的死亡。
- 可是那时虫子已经在果实里了。
-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遇到有些个人或者团体似乎在追求同一个目的,这样就把他们团结起来,说同样的一些事情;但是慢慢地情况变得明显起来,他们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原因就在于意图不同。他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这些不同的团体之间看来具有共同之处的后面各有他们自己的真理,结果明显的是,一切团体所共同持有的是一种或多或少是模糊的概念而不是目的本身。
- 革命的联合迄至目前为止始终是误会而已。
- 不,缺点是在目的之中,是在果实里的虫子。
- 意图是超越历史的。
- 它在历史中出现,却不属于历史。
- 叛乱者或革命者一向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们无法命名或者没有看清楚却想实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正是我们必须设法加以解释的问题。
- 在氏族里我们都是兄弟,与我们都是同一个女人所生是一样,这个所谓同一个女人是以图腾代表的。他们从这个女人的子宫里诞生出来,从这个意义说他们都是兄弟。在这一点上,到底是哪一个个别的女人,不是问题所在。她只是一个女人,有生育的子宫,有哺育的乳房,或者还有负载孩子的背部。这个母亲可能就是一只作为图腾的鸟。
- 神话总是属于过去的。
- 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的“不适”的处境,还有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因为那是所能采取的最简便的一种态度。对于我,法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物。就我来说,反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愉快的事。
- 在某种程度上,示威者需要他的敌人,正像两片嘴唇要分裂就互相少不了一样。
- 这种关于团结的独特观念是否已经标志了兄弟经验的衰退呢?这中间有互相损害的宗派,惰性,对于解决长期潜在问题的软弱无力;在这方面,人们使用了理想的武器:憎恨另一方——1789年的贵族阶级或在伊朗的美国人。实际上,对于统一的明确接受已经停止,而求助于通过攻击以前的力量而产生的这种消极的团结形式,则是掩盖这种衰退的一个方法。这是革命政治的反常运用。
- 当一群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神秘的团体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知道他受到威胁了。
- 我写我所想的。
- 救世主主义是只有犹太人才能以这种态度设想出来的一种重要思想,但是它能被非犹太人利用来达到其他目的。
- 我们永远不会结束战争,我们没有任何目标,只有人民为之斗争的那些个别的目标。人民开始进行小型的革命,但是没有一个为人类而奋斗的目标,没有能引起人类关注的东西,有的只是分裂。